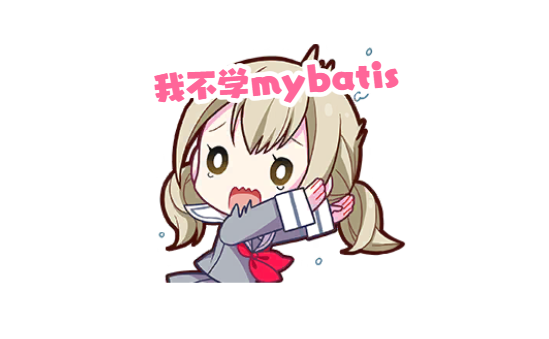死星照命
你眼睛的面积一定小于湖
你也很少哭 可为什么
坐在你面前 就像站在湖边
细细的雾水就扯地连天
我翻看之前写的东西时,总会想:我靠,我到底是怎么写出来这些屁话的。
感觉是即兴发挥的抽象成分太多了,无法复现。有一种早上起来发现起早了,想要睡又睡不着,愣在床上不知道干啥,想打喷嚏又打不出来,想下床又不想动的感觉。
我的灵魂一直在同一个躯体里反复地压缩折叠变形,像是在揉一团只放鸡蛋的碱面。新的血肉层层叠叠覆盖旧的,形似质量很差的3D打印机,藕断丝连,到最后只能糊成一团。
有一段时间,我妄想从自己输出的密集的内容中寻到慰籍、鼓励、救赎之类的东西,然而输出后我只觉得恐惧而空虚,只会变本加厉,本能似地一遍遍模拟着明天和将来的人生道路,担惊受怕却乐此不疲。这些东西就像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在身上的水蛭,偷偷地吸血,被摘掉以后也会留下巨大的空洞。
我总是冷不丁地回头看,然后又冷不丁地发现自己早就已经来到了以前的以后。片刻的抽离感,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眨眼间的狂风乍起——和老友重聚的旅行,彻夜的狂欢与黎明出头的疲惫,随着时间逐渐陌生,离别,再往后是乍起的怀念,恍然大悟原来往日不复,只好又把自己这点小小的酸楚收拾好,浸回时光的腌菜缸。
写这段的时候我才发现,小时候所能设想的最远的以后,居然是2022卡塔尔世界杯。怪不得梅西举起大力神杯的一瞬间,我突然有些恍惚。好像只要所有的故事写到了头,结局就会像一个编译器里的断点,把所有悲欢离合都停住。我以为可以像三毛说的那样,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限广大的日子呢。可是世界这个沟槽的垃圾编译器没有断点,命运只会疯了一样奔腾不息,故事结束以后,还有更多更多的以后,像是不停地出狗尾续貂的续集恰烂钱的垃圾作品。
未来无穷的日子,无尽的路,一眼看得到头的生活一眼望不到头。海子诗里写过,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后面还是道路。
他还写过,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一滴不剩。
收拾东西偶然翻出以前的作业本,好像看到了青春游走的印痕,斑驳的纸面上尽是日夜流转的车辙,纹路走脉,一览无余。
时间实实在在地从指缝里流过,我正在四季轮转的空气里氧化,像一只被咬了一口又放置了二十年的苹果。能被记住的夏天都会熔进身体,春秋冬的时候它就在骨髓里休眠。等新的夏天回来了,它就又带着洗完澡回到书桌旁时,沐浴露,水汽,木头,笔油,空调风的复合气味,弥散在缭乱涣散的记忆里。时间的颗粒度并不是均匀的,人的一生最多经历百八十个夏天,去掉几年的茫然、匆忙、恍惚什么的杂质,其实我们一生真正能记住的只有寥寥几个夏天,不管怎么说,十八岁的肯定算一个,因为我在每一个夏天都会忍不住地回想十八岁的夏天。
以后就会变好了,以后就轻松了,以后是一切的答案,现在的以后,以后的以后,一切的以后,所有十八岁的痛苦都会像变戏法似的,噗嗤一声消失不见。那时深信不疑的我会心甘情愿不厌其烦地收拾自己的烂摊子,一遍又一遍。书桌上铺天盖地的卷子诱发史上最大的雪崩。零落的一把把红叉,横七竖八,落得遍地都是。可是我还是那样的灿烂,伸个懒腰都能抖落一地闪闪发光的可能性。我已经记不清那时我在用什么消遣,出于怎样的想法与观点,用什么填补空虚与孤独。我只记得那时觉得世界太过懦弱轻薄,唯我孤高勇敢。那时看到茨威格回忆录里最后一段话,深以为然,“不过,每个影子毕竟也都是光的孩子。”
我以为,只要我想,我就可以轻松飞越教室,飞越教学楼,飞向克里姆林宫。狂热的心忍不住要冲垮世间的一切高墙,直达最闪耀最明亮的未来。联想到夏天起风的日子,我们学校有个不成文的传承,毕业班的同学们会用草稿纸折纸飞机。我用尽力气,想将它带到最高的蓝天。在窗前放飞梦想时,我只想看到它笔直冲出教室带着自己所有的期望消失在窗户的视野里,此去千千万万里,替我去寻找以后的千千万万个奇迹。
我烧尽绽放的原野,浇灌给期待。
上次回学校,经过那些教学楼,我在楼下看到了一架又一架新坠毁的年轻的心。我猜他们多半也是和我一样,都扑了个空吧。
如今,我亲眼看着“以后”一点一点地挪到了自己面前。原来“以后”根本不是免死金牌,张牙舞爪的关底隐藏boss。
多年以后,面对像山一样横在面前的“以后”,被城管赶得满地跑的码农烧烤老板L1ttleQing会想起老师带他见识"hello world"的那个遥远下午。
我现在才知道,所有的“以后”都需要一个清晰的明天才能稳稳接住。可是啊,可是啊,那些不切实际的期许就像满屏幕乱飞的野指针,过去种种的不甘心,年少的不如意,那些无能为力又痛彻心扉的事情,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怪不了任何人,都是我没操作好,技术水平不到位。它们变成了永远不会释放的内存。数据结构的张维勇老师说了一句我记到现在的话,人生好像一棵不平衡的二叉树。这个论断有些悲观,因为到达尽头前,我们总会不断地1怀疑这一端的遍历是死胡同,树杈最远那一端的选择才是最优的。
现在,高中时让我困扰的一切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尽数钻进屏幕,变成编译器上瀑布一样的报错。IDEA上花花绿绿的只言片语,像是炫目的霓虹灯,闪烁着迷离的光,乱人心神。它们是不是正好能找补秋招金九银十里下落不明的简历。看着密密麻麻的日志,我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感到愤怒,不明所以的压抑,呼吸短暂变成手动挡。情绪错综复杂,绞尽脑汁搜罗词句也描述不出来,有时候像是锟斤拷烫烫烫一样难以识别,有时候就干脆单纯是缺省值,留下好大一块令人心悸的空白,让人不知道怎么去填补。
忘记是哪一天,我明白了自己终其一生所做的,最多就是普通的应用开发,不可能是创新研究。所以我的问题在网上一定能找到,如果找不到,要么问错了,要么思路错了,重新分析方案。总之就是,我知道自己挺普通又自信的,但遇到一个存在多年、多次reopen、现在还是open的issue,还是会心力憔悴。这个issue的内容是怎么好好生活,怎么爱自己。
我的绝大部分想法,就只是像艳阳天里的肥皂泡而已,流光溢彩,晃晃悠悠,载浮载沉,明灭不定,然后突然啵一声消失不见。好想按ctrl+/,把它们全都注释掉啊。
我能看穿内存里雀跃的0和1,摆弄函数和接口,识破数据结构的伎俩,但还看不清那些生活的实景,捉摸不透漫漫岁月的形状。
我真想绕过繁杂往复的电子帷幕,亲眼看看实实在在的人间。所以我又去了一趟川西。
我只用了半天就越过了去年去的最远的地方,感叹怎么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到底是谁在用薄薄的刀子裁剪我窄窄的日子,分寸恰到好处,让我毫无察觉地慢慢变单薄,风吹一吹就吹透了,想流眼泪。我好像永远也走不出去年的记忆。折多河还是一样湍急,折多山也还在那等着我,漫山遍野都是流淌着的云,而呼啸的风正扯满一座塔的彩旗。
去年的川西和今年的似乎是一个样。一样澄清明亮的天,淡淡的流云,十月青黄不接的漫漫草原,牦牛群相似地甩着尾巴。便利店的阿婆似乎和去年是同一个,一样皱巴巴红彤彤的高原面相,像正被风化剥落的岩石。她坐在一样的位置,卖着一样的正宗高原老酸奶。浑身灰扑扑的小孩一样地在一旁追打嬉闹,而我在同样的车窗边靠着脑袋,在同样的318上急驰而过。
好像所有一切都被定住了,只有我到来之后,高原才开始被加载,这里的时间才继续流动。日子变得好慢,好长,一成不变。他们有太多和我截然不同的生活,呈现我难以想象的面貌,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隐秘地展开。原来人生真的有好多种可能性,可惜我们都不能选择另一种生活,我当然有权拒绝一种生活,但是我没能力拒绝。
我也想留在格底拉姆当野人,在鱼子西开观光车,想和他们一起去放牛骑马,想在理塘露出纯真微笑;某些高原的藏民们会不会也想和我一样,去不需要氧气也能好好呼吸,皮肤不会晒出高原红的大城市生活呢?也就想想了。生活太沉重,它的惯性太大。
在洛绒牛场时暴雨倾盆,大伙躲在景区小木屋避雨。这一瞬间我从去川西追寻自由的说辞里短暂抽离,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摆脱自己面临的任何一种困境,旅行就要进入返程阶段了,我会很自然地回到原本的生活里,那些希望逃避的事情会随着海拔的下降变得清晰,什么都没有改变,仅此而已。我望着云雾里的仙乃日、央迈勇和夏诺多吉三座雪峰出神,神话里有比天伟力的它们如今纹丝不动,缄口不言,只有亘古的沉默在我耳朵里炸开。
我给我妈发消息,说稻城亚丁在下雨。我妈说高原下雨很正常。顿时想起百年孤独。我是在七年前补习班里用午休时间看的百年孤独,那时年少春衫薄,如今一晃七年过去了,我以为自己早就不再多愁伤感,可是现在却仍然被这样磅礴的巧合击中。
“奥雷里亚诺,”他悲伤地敲下发报键,“马孔多在下雨。”
线路上一阵长久的沉默,忽然,在机器上跳出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冷漠的电码。
“别犯傻了,赫里内勒多,”电码如是说道,“八月下雨很正常。”
时间这台大机器散架了。
小时候暑假,每天晚上吃完饭就出门疯玩,玩到天慢慢黑下去。傍晚时分的滨江广场,太阳斜斜地洒下好暖好暖的光,质感就像是刚出炉的烤红薯。我望着涪江夕阳下粼粼的波光,看那些云母片一样亮闪闪的光点浩浩荡荡流向水天一色的远方,一去再不回头,只有几只水鸟隐隐约约在天边闪烁。
那是个多好的傍晚,树一点点高,鸟一声声叫,我的影子在斜阳下晃晃悠悠地漂在水上,眼前的一切都灿烂明亮。我跑来跑去,和小朋友们在暮色四合里穿梭往返,舍不得回家。一玩就忘记了时间,总觉得什么看不够,怎么都玩不够。
我爸说,要看够玩够,那还得了啊!那可就长大了,差不多了就回家吧。于是这时我转身回头,路灯亮起来,夜幕拉上去,我们慢慢悠悠往回走,像来时一样。那时身边的江风软软的,像泛起水汽和草叶的味道的拥抱。江的那一边千灯万盏,好像是从水里浮起又沉下去,水波把它们打碎又重组。影影绰绰的岸边,我的每一步都踏在未来的回忆里。涪江在我身后徐徐消散。那一天,心底突然生发出一种莫名的悲伤,是关于爸爸说的长大吗。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在回忆里不断证明。终于忘记你的时候,你出现在我的梦里。
什么时候那些沉寂的温暖可以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变得鲜活呢,其实我一直在暗中期待,某一天,那时的斜阳可以又升回江边的天空,我可以像小时候一样,重新再来一次一模一样的日落。我真正需要的,或许就是这样平常却又弥足珍贵的温暖,它们能在漫长岁月的每一个皱褶里熠熠生辉,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如果没有滨江广场旁一排排熟悉的红漆面房子,没有扬起又落下的尘土,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江风,谁会证实我以往的生活。可是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风雨飘摇,谁又能见证。
我已经是升级版的自己了,很多特性和历史版本已经不兼容,几乎不可能再溯源。于是我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浩荡时光里一个离家出走的远行客。
我突然感觉到喘不过气来,生活二字在丹田处骤然升腾,直冲到脑子里。它以350TB每秒的速度被上传至云端,然后又以600TB每秒的速度被下载到一些去中心化的时空里。
我想起那时甚至没上小学,最多四五岁,想要和小朋友们一起去吃旺旺碎冰冰。可是我没有钱,爸爸妈妈也没带钱。我左顾右盼,然后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无计可施又无济于事。我已经二十一岁,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无计可施,理解了无济于事,所以不再放声大哭了。
也是那时候,偶尔晚上睡不着,婆婆会陪我聊天。很难想象那时睡不着的只是因为白天太兴奋了。我讲学校里追逐的笑声,和朋友打闹的惊险,小卖部里新奇的玩具;婆婆给我讲市场涨了两角的豇豆,隔壁大爷大妈家里的琐事。听不懂,但不知不觉心里就轻了。“早点睡吧,明天带你去吃米粉。”米粉真的很好吃,我现在也还是很爱吃米粉。
想起一年级的寒假,书房开着暖气,有铺了毛毯的椅子,我在摩尔庄园里把烂番茄砸到那个冲我扔雪球的人头上,然后扭头和身边观战的爸爸一起哈哈大笑。
想起初中,某次考试考的很糟糕,有道简单题全班只有我一个人错了,数学老师气笑了,过来揪着我的耳朵说,你看看,辣不辣眼睛?可是我就是不会做,我说有点辣,然后大家都笑了。那时教学楼外面的天黑蓝黑蓝的,我的胸口闷闷的,被骂的时候没哭,走在路上,看到路灯刺眼的光,突然无意识地泪流满面。
想起高中,偶尔我会早醒,爸爸妈妈还没有起来。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那是每周都听的华北浪革专辑封面的蓝,心里的疏离感和自由感交替着爬上来。小区里传来几声鸟鸣,在它变成很多声之前,我就又会睡去,等到六点半出发去学校再醒来。
我想起刚满二十岁的时候,站在西南大学橘园八舍113的镜子前,踌躇满志,试图发起一场盛大的冲锋。
想起二十一岁的我,在稻城亚丁短线尽头珍珠海的岸边上坐着。我用手遮住太阳,看着雪山,在湛蓝的天空下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所有的事情总会好起来的。
科学研究表明一个人的脑容量只有2.6MB,所以整个云同步的过程持续0.03微秒,0.03微秒之后,我返回当下,两手空空。
“我围抱着火炉,烤热漫长一生的一个时刻。我知道这一时刻之外,我其余的岁月,我的亲人们的岁月,远在屋外的大雪中,被寒风吹彻。”
文字于我即是快马、长枪、大碗的酒和阻绝兵马的群山,可以让我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短暂割据一方,当一把土匪,然后被现实迅速剿灭。这是内在的狂欢,平息后即归于日常。时至今日,因为已经读过了好多书,我的情感阈值已经大幅提升,对浓烈的文字有种近于自我保护的屏蔽,越来越少被深深触动。可是写到这里,以前读过的这些东西,像是哈利波特的闪电伤疤一样,突然就疼得发烫。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漫漫的岁月原来是雪一样,纷纷落落。趁扬眉的功夫,它正好就能掉进抬头纹里,压出一道道好深好深的沟壑,横贯我似有若无的记忆,深得足以埋藏一大半侥幸的童年与仓皇的青春,足够掩饰孤独,歧视与荒芜的爱。潦草的旷野,不待解释的失败,混乱的眼泪,匆忙的失去,成批量的无疾而终。
人的生活总是看似丰饶而又格外空旷,靠着二十年前的生命,十年前的梦想,五年前的回忆,一年前的衣服,三个月前的项目,昨天的作业,中午的拼好饭,以及因为塞满了期待而变得越来越重的的未来堪堪支撑着。
临走前,我把以前的自己深深掩埋在贡嘎的积雪下。从此我不记得他,狂妄的他。
芒草在山巅,痛苦都留在眉间。
有时我很爱看自己的手。一些人相信,手上矛盾密布的纹路深埋着自己的命运,能以隐秘的形式断言未来百年分支蔓生的光阴,这样就可以自作聪明地逃避虚妄的思考。
我倒是觉得,它们更类似于江河的形态,起落流淌,浅浅泛起细碎的过往。
似乎认同了这样的解释,实质化的命运就能服服帖帖地在指间闪烁跃动,辗转腾挪,严丝合缝地运转,像啮合的齿轮。
汉朝时,蜀郡有口怪井,井中常年冒火,在国运兴盛的时期,火势很旺;汉室衰微后,火渐渐小了。后来有人投了一支蜡烛进去,大概是想引火,那火却灭了。那年蜀汉灭亡。
帝国的命运正反映在千里外一团颤动的火焰中。汉武帝在上林苑中策马奔腾,驰骋射猎时,对此毫不知情。
我喜欢这个小故事,我想,人对自己命运的掌控,只是迟钝反射弧下的暧昧的幻觉。一生的风沙星辰何其辽远广阔,不可能被简简单单地攥进拳头。
我感到一种近乎抽象的哀伤,哀伤没有想象中的持久。有点惭愧,惭愧也转瞬而逝。和那年背后的涪江一样,消弭于无形,好像那只蜡烛之于蜀汉。只是我偶尔也还是会感到眼底潮湿,是心底贡嘎的积雪消融,还是身体里涪江的潮汐又拍上了岸头。
带我回去吧,我想找到十八岁夏夜的灰烬。
天地轰鸣,此消彼长,死星照命。
青春已复过,白日忽相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