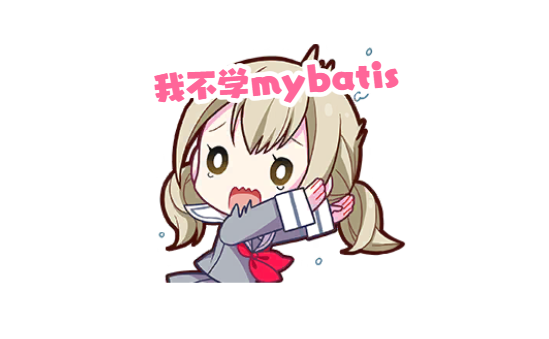呼啸着萍水相逢
我们不要在这里
跟我回去十八岁
躲到台大校园杜鹃花丛下
不要被命运找到
——简嫃
记得千禧年吗,也不过就是二十四年前。
我爸妈说,2000年到来的时候,大家满怀期待又不知道怎么庆祝,于是就穿上最好的衣服,在街上从这一边走到另一边,再从另一边走回这一边。
每一步都踏在回忆里,越陷越深。就像昏沉的暮色一点点染上他们的心头。
直到他们给我讲的时候,世纪之交的夜幕才真正覆压下来,在我的心里留下模棱两可的轮廓——很多优秀大学应届毕业生一个月工资,居然可以买北上广深一平米的房子。
岁月太远,回音太慢,姗姗来迟。世界终于开始变成一句含混不清的旁白,所有的记忆勾连起来,带动过往的片段和当下的余波,流转不息,翻腾汹涌,潮起潮落。
大部分人都很乐意主动卷入往昔的漩涡。我怀疑,这是因为记忆是为数不多的、完全被自己掌握的东西。这样我们才会忘记,自己身上窸窸窣窣流动着的光阴,其实或多或少遵循着和别人雷同的轨迹。
一个人的回忆该到哪里为止,是离亲人最近的房子,大地与远空的交界,故乡飘渺的云瓢泼的雨,还是地图上往复重叠的经纬线,有时候我也会忘记望山跑死马的故事。
我太喜欢这个标题,好有隔阂感,像附着在列车车窗缝隙里擦不掉的灰,像整个00年代弥散着的毛玻璃滤镜,妈妈小灵通吵闹的彩铃;像过时的效果器音效,空舞厅里的灯球,沉默的皮衣吉他手,DVD切信号前的短暂花屏。
像下午三点的阳光透过钴蓝色的玻璃照在蓝色花纹的地板砖上,小狗呼哧呼哧吐着舌头,动画片声音很大。像搬家离开涪江边时,那样的阳光明媚。像是那天你在阳台说下次一起玩,可我在楼下等了十年,还是没等到你。
像是那种夕阳将落不落时,光影照在主唱的身上,吉他和贝斯手的剪影投射在旁边的幕布,空灵的嗓音和配器响起。像是没带伞又必须奔跑的雨天,全身感官都无可奈何地兴奋着的感觉。迷迷糊糊的,会让人联想到一连串很多年之前的东西。
EVA,涪江,赛尔号,在建国门打棒棒的圣诞节,挑担卖豆花的老人,三光街的专业卤鸡蛋,人民公园的少年宫,小卖部的卡片,肯德基的优惠印花,平安夜的兴力达百货。
千禧年,世纪之交,那个时代脱胎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终结于10年代的互联网爆发,总共只维持了10年甚至更少的时间。夹杂在虚拟经济诞生和实体经济升腾的交接点。
而在这样狭窄的时间缝隙里,只有很少一部分像我一样的孩子,拥有过这样的记忆和童年。在短短十年内看到曾经朴素简单的生活环境突然变得拥挤喧嚣。特别是互联网,它居然会有方兴未艾的时候。在今天,这简直不可思议。
向前的长辈们,普遍没有什么深刻印象,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他们有更重要的事要操心;向后的后辈们,则是直接出生在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外置器官,他们无法理解流量要省着用,想象不到上网还需要按一下连接宽带,甚至极端情况下要使用拨号连接的生活。
一个时代的记忆居然只存在于我们那几年出生的孩子身上,这样的情况绝无仅有,也弥足珍贵——我们还来不及等待老年,就开始怀念曾经那个时代了,因为它不曾出现于长辈的口中,也不会被之后的小孩子们提起,它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像一场发烧时做的怪梦,光怪陆离,醒后就不再记得。
既繁荣,也原始,既保守,也开放。我对千禧年代只有一句想说的:我不在乎天长地久,我只在乎和你们曾经一起拥有。
一晃眼,原来世界已经迭代了二十年,我也早已经不孚众望地,长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人。多年以后,与成长的世界再相逢,檐上旧巢不见雀鸟踪迹,檐下人到哪去,这封信怎么寄。春日部市的风吹不到翻斗花园,我们也永远不会再见。
如果把老房子拆了,修起一座一模一样的新房子;买一件新衣服,穿破大小相仿的几个洞;找回旧玩具,接着编他们无休无尽的冒险故事;儿时的燕子,是不是也会一模一样地飞回来。
要是这样,亲人们也还不老,你和朋友们也还那么小,那么擅长飞跑,脚程快到无妄之灾再也追不上你。
上次回西山公园,充气蹦床摊位的老板居然还记得我,指着我大笑:一转眼你长这么大了,你小时候每次都一路过这里就吵着要来玩呢,你爸爸妈妈都拿你没办法!
回忆有不稳定的花期。
回忆泡在千禧年的福尔马林罐里。
想起之前,学长讲给我的求职经历:几乎每一段人生经历都要交代清楚,有一点异常那就完了。几遍下来就很机敏地学会规避敏感词,不讲蒙太奇式的谎言根本找不到工作。于是那些经历渐渐变得模糊,真的假的都揉在一起,慢慢连自己也分不清,连自己也深信不疑。
而世纪之交,也就是2010年前这段时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被问到,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记忆里闯下弥天大祸,把真正的自己安安稳稳地藏在这里,它像一个巨大的避难所,童年永驻。它很安全,只会未知,不会变化。
那时的太阳碎成一块块,云聚成被子铺在天上,风在涪江里游。绵阳晚七点的时候,人人都往有灯亮着的房子里赶。三轮车叮叮当,汽笛悠远,东方红大桥上的肚子不少是饿着的。滨江广场的灯一瞬间亮成一条远到天边的线。
在书房伸个懒腰,不知道该玩什么了,我也不想关掉电脑,一边发呆,一边想什么时候吃饭,电脑不用关,吃完了可以接着玩。
楼下的滨江广场,从过去到未来都是一个样,猫在一排路灯的黄光下缩成一个垃圾桶。白天出太阳,晚上有月亮,我夹在中间,是一片星星。窗外江风正缥缈。每次打完游戏,爸爸会让我去看看远处休息眼睛。在阳台上眺望远方,心上一件闲事都不挂。
那时他还不知道,在不算遥远的未来,他将经历什么样的波诡云谲,他会怎样跌跌撞撞地晃过一程又一程。他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让他成为了什么样的人。
就像所有故事一开始的那样。
我想和他说声抱歉,不好意思,把你设想的未来走得乱七八糟。
我现在还经常梦见奶奶家,也就是科学城八区,某个夏天,凉爽的清晨,一场阵雨将歇,青草和泥土的气息,就是下雨的味道,漫到我床前。我躺在凉席上,外放着《稻香》的前奏,奶奶说这歌还怪好听的。周中爸爸妈妈上班,我在八区和小朋友们一起疯玩。至于周末,我不是骑着小车在人民公园的城堡里横行霸道,就是在富乐山的竹林里打真人CS。
后来在园艺山读书,一直很想回去看看。等到我终于有空自己回去,才发现我想回的不是奶奶家,不是人民公园,也不是富乐山,而是那个能随便浪费时间的时候——平时有人会喊我去楼下玩,周末可以选去人民公园还是富乐山的时候。
走在涪江边,呼啸的江风拥抱我,我和自己萍水相逢。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长大以后,我极其缓慢地意识到,世界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的一切终于都由自己掌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人管得住我,我随意贯彻自己的意志。
我爱说实话,一开始真是给我爽完了。
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我对未来一点计划都没有。所有的计划,都无一例外地,整齐地,不约而同地,停在了高考完的那个夏天,我正好十八岁。好像被切断世界的那道斩击命中,人生在2022年的夏天腰斩。
我十三四岁左右混迹贴吧的时候,怕人家觉得我小不带我玩,都骗人说我十八岁。我好想早日十八岁,这样就可以再也不被管着。十八岁就是我想象的极限。现在想想,十八岁居然已经离我越来越遥远了。很奇怪吧,我甚至根本没准备好活到现在。
那时我还完全不知道,没人管的住我,也就意味着今后做的每件事、每个决定都不打折扣地记在了我自己的头上,而且无一例外,都会对未来造成不可挽回的持续性影响,或好或坏。从此不会再有谁为你清澈的愚蠢负一丁点责,基本所有人都只会说好死,开香槟咯。
以前做错事的代价只是承认错误,再挨一顿骂,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好了,没事了,玩去吧。每个学期一开始,过往的记录几乎都被清零,像是新赛季整个重置。退一万步说,哪怕吃了个留校察看,等到高考前肯定也能被消掉。
有时也会想起,高中有很多自我感动着发狠的通宵,妄想凭着一腔热血就能掀起风暴。我自顾自地以为只要再多努力一点就可以了,再多一点,多一点。只会多刷题,现在看来就是方向性的错误。可是高考前犯多少错都无关紧要,高考前每一次考试的成绩都只是试错的一部分。我是杀红眼的赌徒,下注的零成本让我有底气一输再输。我好怀念那种无所畏惧的感觉。
对未来的孤注一掷,从今以后,不能再是赌气,不是说只要幻想自己有弄潮的命,到中流就能当上砥柱,浪遏飞舟的事是开不得玩笑的,被水冲走了可没救生员。以后没有方向性的错误经得起反悔,许下的承诺也不能随随便便烂尾。
拿打麻将举例子,小时候打纯计分的娱乐牛马场,现在突然打上了真算钱的,才发现原来自己根本赌不起,谁若赢了,我只能故作镇定地祝贺你。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先前的我都不知道真正的失败应该是什么样,我所经历的失败都并不彻底,都是可以被某种手段弥补回来的,我经历的挫折也都是狐假虎威的半吊子罢了。那时的所有悲伤痛苦绝望,都在可控范围内,都是能在某种程度上预见的,它们其实是对现实的拙劣模仿。
所以那时才少年得意,春风满路。
所以现在才举步维艰,踟蹰不前。
有时我会想,要是我一开始就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像个凑数的NPC,凭空刷新在三线四川小城,蓝得不像话的天空悬在上头,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去了解,就安安静静地看着,日子一会繁忙一会悠闲,细水长流,四平八稳。
可是现实是,所有的责任,对自己的,对别人的,都已经被狠狠地甩在了我脸上。从富乐山到缙云山,从涪江到嘉陵江,我真的走了好远。现在开始,不行真的就是不行,不会真的就是不会,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没有理由,不找借口。生活绝对不会放水,这个世界旋转得飞快。
人也再不会像高中时那样,直来直去地受伤——心就和一块玻璃似的,脆生生地碎掉。现在的伤痛更类似于锈蚀、腐烂、低温烫伤,局部坏死,温和地、毫无痛楚地,越来越麻木,越来越迟钝,直到某一天,让我再也说不出“我到了一百岁还可爱”这种话。
人生像遍历一棵有序树,从根节点开始就处处局促。还没来得及释怀,就又要被迫去面对下一层子节点刻不容缓的选择。好复杂的递归,我真想不明白啊,要是在命运的岔路口前,我能更主动更勇敢一些,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只是想这些也没用,以前的我既不会数据结构,也不会算法。虽然现在也不怎么会就是了。当然,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的意思是,在桥头直视船的时候,所有船都是直的。
前几天我妈给我发了一堆老照片,里面有很多亲戚年轻时候的样子。还找到了一张笑的很开心的我。在书房的电脑前,打游戏的我回身比了个耶,没心没肺的。
突然想起余光中的一句话,令你悲伤的一切,暂时都还不属于你。
那时候玩的是宝可梦叶绿,我最喜欢的宝可梦就是皮卡丘。学着小智配招,带电磁波打人,可以麻痹对面的宝可梦。看着对面出不了招而我可以打两回合,小小的我哈哈大笑。而长大后,常常有不知道躲在哪里的人对我打出电磁波,让我麻痹在书桌,在大街,在地铁,在床上,在梦里。
我在这里应该写一点热血或者冰冷的句子,但还是算了。一方面是因为,将一堆杂乱的思绪加工成一段没有语病的话,已经成为现在的我的奢求。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都是CD很长的技能,前摇后摇也都很长,我要捏在手里,下一波ALL IN狠狠地打一次爆发。
毕竟再过两年,我好像是会变成那个近战兵啊,开局的时候被精心安排卡着挨三个远程兵打,对线时的主要作用是拉扯抗塔爆金币,打团时就被不明AOE爆了埋在中塔。我就爱偷吃点塔皮,半死不活的塔你不打我也不爱扛。
“春风若有怜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我已经很难在不笑场的情况下念出这样的诗句,“终不似少年游”,只有少年念出来才会意气风发。从任何角度来看,我已经不适合当热血少年漫画或青春伤痛文学的男主角了。
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事实上,我还勉强算是少年,还算是个学信网可查的大学生。但是每每走在沉沉的夜色里,夜风灌满嘴的时候,我也总想纵声长啸。
回老家的时候,看到一片笔直的人工林。家里人说这是桉树,长得非常非常快,但是对环境破坏很大。从播种到砍伐只需要几年,而这短短的几年里,它们会榨干土地里所有的养分。
仿佛看见了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摆弄被左右的命运,透过劳碌规矩的一生一眼望尽惶恐困顿的晚年。“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这句话突然冒出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居然是高中积累作文素材时埋下的伏笔。
说到作文素材,看到过这么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能看到烟。”据说是梵高写的,我不太信。又想起黑格尔的那句“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我那时非常中二地设想,自己读书的样子就像一个风雨飘摇的浪客,独自行走于莽莽荒原,漫漫长夜,看见一株悠久的火苗,于是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地燃尽自己,最后成为历史的一堆灰烬。
朋友听后不以为然:“你cos的是梵高还是黑格尔?”
我也曾让理想就地生根,凝聚起脚下土地中所有的勇气和希望。毕竟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在短暂的青春里,我做的所有事,其实只是拼命埋头汲取营养,寄希望于生长成材,参天凌云。
如果生活为你关上了一扇门,你就应该去打开它,关上的门就应该是要被打开的,这就是门,门就是这样用的。
对于开门这件事,有些人会问,这种情况下可以去打开一扇窗吗?
这就好比在说,程序员掉的毛可以换成腿毛吗?
很显然,不可以。
世界的迭代越来越快,一个终日缅怀往日风尘旧影的人,愈发显得荒谬而不合时宜。比起二叉树的非黑即白,现在我更相信人生像一个跳表,或者说更像有向图——更多的方向,更多的可能。甚至百般曲折后仍然殊途同归。
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事,有特定时间要去争取的东西,不严谨地说,我只是装模作样,怀古伤今罢了,不是真想念过去,而是借着回望过去的这股劲对现在说,我燃烧你的梦,我诠释你的码。
举个例子,高中毕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再没写过什么东西。刚上大学碰上疫情,每天的生活都像缓慢行走的干尸。突发奇想写博客也只是想让自己能有点事干,偶尔还能反思内省,发发牢骚。虽然读理科,但我其实是喜欢文学的,要不是文科就业率太感人,当年差点读了文科。没想到现在还能写这么多东西,还有人乐意进博客看这些文字垃圾,感激不尽。既然你们都看到这里了,我提一嘴,文章下面有评论区,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总想着到时候,总没到时候。
万事不回头,毕竟难有头回;往事如水流,始终空送流水。世界好大,时间太长,我只能寄希望于未来,遗憾的事终究会款款重写,错过的人一定会再相逢。老人坐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我们划开没有通知的手机,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想见和能见的人都在这里。
所以说,我还是喜欢吹弹可破的当下。
本质上,我们成长在每一场萍水相逢。
在长大后的漫长岁月里,我还是想做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你要做一朵花,才会觉得春天离开你;如果你是春天,就没有离开,就永远有花。春天是长在骨子里的。
写得好乱,可是改也不好改了,想卒章显志升华主题也完全失败,既然是将就着写的,将就着看得了。
带我到很久很久以前
消失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过了期限
带我到很久很久以前
消失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某个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