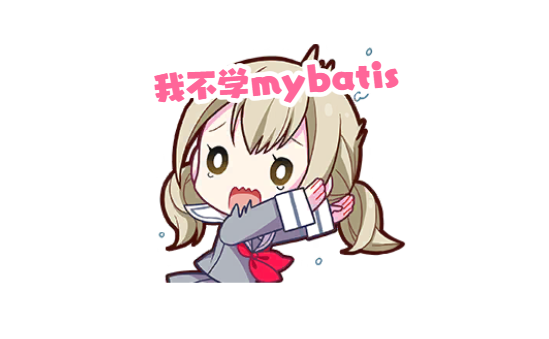在每一个瞬息
这些承载着鸡零狗碎的文字
和我本人是一样的笨
用力、无趣,留不住乍现的奇迹
情绪鼓荡,战战兢兢起起落落
此行的终点是大海
我是一条船
周五下午就没课了。迈过吵吵嚷嚷的大街,我缩回埋在地平面之下的宿舍。坐在不太宽敞的窗前,看着刚刚落日但还没完全黑下去的天,拿出剩下的半瓶尊美醇,一口一口,可以喝到天完全黑下去。
这样,酒精和心情,全都看不清分不清。
天气转凉,阳光越来越像棉絮,盖在身上真的很暖和。这种天气,非常适合躲在被窝里做很长很长的白日梦。暖融融的梦里,未来的一切不仅美好明亮,还唾手可得。这样很容易让人忘记,其实自己连咬咬牙一个鲤鱼打挺钻出被窝的能力都没有。
生活没走上正轨,要不卧轨吧。
彷徨的时候,整个生活单纯是在高位截瘫。人只会翻来覆去地想,谁来帮帮我,有谁可以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带着自己义无反顾地逃离奄奄一息的年关岁末。
因为脚伤了走不动路,我请了整整一天的假,睡到中午才起床,躲在宿舍里打开电脑,开始猛猛刷题。
写完一道力扣题解,我偶然跟着评论区里前辈的脚步,第一次打开了Codeforces,接着第一次知道算法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第一次知道rating分是什么东西。
在网页加载完毕的那一刻,我突然回头四顾,大伙都上课去了,宿舍安静得不像话,我自己呼吸的声音仿佛某种神谕,一种感觉紧跟着强烈地爆发——我没来由地意识到,这一瞬间,几乎注定会被今后的我无数次回访,好像命运就将要从此处开始汹涌奔流。所有的未来都指回这个似是而非的奇点。而我呢,另一种形式的众目睽睽之下,一无所知,只身打马,糊里糊涂地行走在故事的序幕里。
我得把这一幕收拾起来,多加点盐,腌起来,等老了,好下酒。
几秒钟的愣神以后,我开始带着点赌博的性质搜罗起词句,试图拼凑起那一瞬间的印象。可惜照猫画虎,越描越黑。不得不承认,很多最细微的感觉是根本不能诉诸笔端的。文字的质地太坚硬,最飘忽的散文终究是实打实的白纸黑字,哪怕最灵动的诗歌,也不会真的从纸上跳出来,在眼前流转不息。史铁生说过的,一旦变成文字,它们就不是它们了。
是不是可以认为,存在一个客观事实,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事情是文字记录不下来的。试图用文字捕捉瞬息间的意义,我总会忍不住细细斟酌字句,想要达到形式上的完美。但要是太注重记录的形式,就会不可避免地经过情绪滤镜的再加工,好像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就难免掩盖食材的本味。这就是在忘却那个值得记住的瞬间本身。
我深知我自己这一支笔太无力,根本笼络不住像烟花一样炸开的灿烂瞬间,最多小心翼翼收集起散落的余烬,以此来纪念那些惊鸿一瞥的灵光乍现。高中那会为了做诗歌阅读,装模作样地看过《二十四诗品》,什么都没看进去,只知道里面写了很多意象,无一例外全是以物喻物。或许是因为文字的笨重定义实在留不住诗意,像是再密的筛网,总也留不住流水。
没关系的,我告诉自己,今后要允许自己在那样一刻发生时,就愣愣看着它发生,只要知道那一刻我曾亲历,就好。
猝不及防的热血沸腾,冷不丁的浪子回头,属于我的尤里卡时刻。那样的瞬间,就好像万千灵感凭空流进血液中沸腾。灵感是状态的流露,我一般在半夜听摇滚时最有状态,状态一过,就再也写不出了。灵感是七岁时那只再也抓不到的蝴蝶。我改文章,往往难下笔,越描越枯,不如不改。状态是不可以欺负的,任性之极,就是丑,也丑得有志气。其实我怀疑,这是因为是我的思维从来没有连贯过,总是在害怕这次写下的其实是某次写过的。
为什么会害怕呢,因为文学性已经一丝一缕地缠绕在了我世界的基本结构上。
某个哲学观点说,我们不能在同一时刻全部看见一张桌子上的东西,所以我们从来不能看见任何事情的“本来样子”。这个世界,与雨果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是同一个吗?
很多人都说,我的文字带有某种灵气,这一点我不否认,因为再否认就显得我像个不要脸的大尾巴狼。
这种所谓的灵气,我认为更多指的是对具体词句的精确把控,清楚文字间细碎隐秘的差别,遣词造句就像中医凭感觉抓药。这大概来自一直纠缠我的文学性。与其说这是一种令人羡艳的天赋,不如说这是某种后天培养的慢性疾病。
很抱歉地说,我对语文补习班一向秉持嗤之以鼻的态度,特别是作文培训,简直是天方夜谭。直到现在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我仍然认为,对文字的感觉是不能讲给别人听的,那是落地就消失的人参果,置我于江湖骗子的地位,就像试图用科学解释巫。。所以这篇文章大部分也都在鸡同鸭讲,简单来说,是在纯扯淡,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
写到这,想起初中见过个哥们,大眼镜小眼睛,瘦瘦的,刻板印象里的典型文艺哥,他写的东西非常跳跃,好像那个半人马座燃烧的星门。他喜欢没事夹着本拆了封皮的书乱逛——很多时候,看书是一个特别好的托辞,因为没有人知道你看的到底是校花的贴身高手还是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于是他们会在心里取两者均值作为你的印象分。他有个怪毛病,这估计是他的最爽时刻top1————见人就问,你看过浮士德吗,你懂浮士德吗。
我说不懂,不好意思,我看郭敬明来的。
高中侥幸发表过两篇文章,居然有人拿着篇文章让我指教指教,硬着头皮看了一眼,直接被文采奕奕的词句吓晕,类似于铁马是你冰河也是你。辞藻华丽我看不完,句式整齐我数不尽。我也不好意思装模作样地教训他,说些文以载道之类的东西,说你写成这样还不如买本词典来随机存取呢。归根到底,文学是一种症状各不相同的病症。有人就喜欢特立独行于他人的疏离感,用书本筑起高台,自顾自遗世独立。有人喜欢把玩音韵,遣词造句,愉悦精神,无可厚非。焚琴煮鹤,有辱斯文,其实也并非我愿。但是一味抱着脱离实际的虚空幻想,言之无物,卖弄风雅,就是你的不对。
于我,文学应该是回家的漫漫长路,而不是营造优越的利刃,更不应该是呻吟的材料。鉴于我已经病出可以指点江山的幻觉来了,我的情况显然更严重。关于我的种种症状,文字本身都比我更有主张,它们总私自给的人生我开出一张张荒唐的处方。每次把那些想到的金句妙句打出来,藏起来,都有一种大病初愈的畅快。
文学性唯一的好处是,给了我按自己心意来解释世界的权利,这就是说,我可以信手撕裂脑海里的现实,接着任凭春风缘隙来。我能肆意解构身上的一切苦难,消弭一切意义,或者在字里行间扭曲纷至沓来的悲伤,也可以摆弄过往的回忆,在主观上去定义某些必然而隐秘的联系。可是越试图编织现实,就越摧毁情绪的稳定性。就好像一把匕首,越锐也就越脆。很难解释。怎么维持精神状态的稳定呢,答案是多读书,随便什么书都行,从书里找到答案,然后生发出更多更多的问题。现在我才知道这根本就是饮鸩止渴,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
这导致我的阅读在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完全混乱的。常常是在这一方面发现超出了理解的范围,又去补另一方面,却发现在那一方面又缺少必要的基础。后来,知识结构就变得奇形怪状,面目可憎了。这就好像是以前为了应付考试,强行将一些并不怎么相关的知识串成一条线,老师说就照着技能树一级一级的点,等你点满就毕业了。
可是读书这件事似乎不是这样的。我文学读的太多,任何文章读一半,就能嗅出行文里可能存在的异味。而读哲学时,又因为历史读的太少,常常抓耳挠腮。从连环画到童话书,从通俗小说到严肃文学,然后头也不回地顺着文史哲的不归路滑下去,我一路读到只能以pdf,txt格式存世的某些不可名状的东西去,这个过程太顺理成章,太自然而然,似乎只是在贯彻一次平常的呼吸。
很不幸,我已经被文学性侵蚀入骨。我的文字真的来自四面八方,经天纬地。它们是我读过的一切,包括但不限于小说,杂文,课本,漫画,牙膏背面的说明,小卡片上不可名状的文字,总之遍地风流。对于这一点,我自认为很幸运,因为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比大部分人都清楚好文字该是什么样子的,毕竟好的坏的我都读了不少。
高三,我每天晚上都回家,但是从来没做过作业。都是读点闲书,读到十一点半,每每临睡前,就把好的文字从脑袋里翻出来,抖抖灰,拾掇干净,放在枕头下,期待着什么时候它会撞进梦里。
王小波在《未来世界》的自序中写道:“在写作时,讨厌受真实逻辑的控制,更讨厌现实生活中索然无味的一面。”他是一个热爱用想象力去创作的作家,而且极端地簇拥有趣。在王小波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我认为在生命中最可珍视的三个元素:智慧、自由、乐趣。
闲得发慌的时候,我总是会想起一件事,北野武先生能在有生之年得到一句话,“日本电影的未来就拜托你了”————这是他最所崇拜的黑泽明先生的肯定。
当然,我现在还不能对王小波说出与北野武先生为黑泽明先生祈祷时说过的类似的话:“如果您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东西想写的话,就让我代您写吧。您就把我当替身为您写东西好了。”可是我就是想。我想变成他那样的有趣的人。
高三,每次晚自习倒数第二节课下课,我总会走出教学楼。吹到晚风的时候,我都能看见,一路的灯光,就那么细细簌簌地打落在这栋我栖身三年的小楼上,我想,这个世界或许还有那么点诗意吧。我认为这个世界很需要文学,起码对于我这样的老鼠人来说,是需要的。
程序员要学会一个道理,不要反复造轮子。所以我要大段地引用王小波的话了,因为我写不出比这更好的。
“在冥想之中长大以后,我开始喜欢诗。我读过很多诗,其中有一些是真正的好诗。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是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于是我开始存下了一点希望——如果我能做到,那么我就战胜了寂寞的命运。但是我好久好久没有动笔写,我不敢拿那么重大的希望去冒险。如果我写出来糟不可言,那么一切都完了。”
看过一篇童话,森林举办选美大赛,小乌鸦黑漆漆的,被大伙嘲笑,不敢去参加选美了。于是它搜集起其他鸟的羽毛拼凑在一起,看起来也像那么回事。最后小乌鸦的羽衣被弄散架了,只好灰溜溜逃跑。我小时候一直耿耿于怀,小乌鸦明明是自己找的大家不要的羽毛,怎么就要被欺负呢。没想到后来我也变成这只小乌鸦,不敢展露自己文字的半点锋芒,总是四下搜刮零落的字句,把那些熠熠生辉的碎片捡起来,镶嵌在自己的句子里,这样多多少少显得明亮些。我的修辞,大部分时候是从海子那里偷来的皮毛,感觉也带有一点木心的成分。至于音律和词句,大都来自余光中。格调,有一部分是史铁生,而另一部分下落不明,疑似是金庸。而文风,很不要脸地说,是当了王小波的门下跑狗。总而言之,写东西时,我无时无刻不是别人,在每一个句读,每一个顿挫里。
博尔赫斯说,你不过是每一个孤独的瞬息。
其实我也明白,我明白,所谓的时代里的文艺,不过是包装精良的文艺故事把我整魔怔了。这是一种纯粹又空洞的可能性,只存在于臆想里。文字是背负着我的一部分却又永远逃逸着我的流星。它让我的心中永远存在漏风的豁口,不断糊上的窗户纸,不断地破掉。如果文学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我会说是“潦草”。
是的,我也曾把勇敢面对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当个文艺b,但是真的不够。面对突然来临的冷空气,最好的办法不是看《百年孤独》,共情遥远的马孔多萧瑟的故事。而是添几件衣服,然后多做点运动,吃点热乎的,睡个好觉。
看过一篇小诗,写烟雾缭绕的寺庙里,一个小女孩在望着双眼微闭的观世音菩萨说——菩萨呀,祝你身体健康。
那么,文学呀,我祝你永远不死。
居然赶在元旦前把这篇东西写完,收笔的一瞬间突然想到,戴拿和盖亚,是一个双押。
就写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