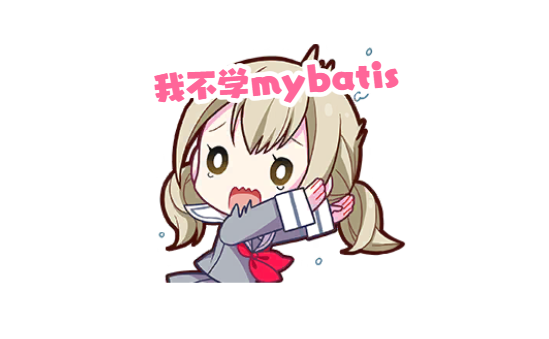凌晨一点遗事
你这艘脆弱的木筏 归处是哪里呢
是人群 还是行迹隐匿的月亮
你要飘流到哪个方向呢
要逃走的话 就在夜色的掩护下
你要去告别吗
与你的过去
与你的身体
凌晨一点被室友微信骚扰。
他说你床上怎么还亮着灯,我说我喜欢熬夜燃烧生命,这样明天起床就有一种涅槃重生的感觉,还有你不也没睡?
看过一个说法,年轻人熬大夜只是把七十岁的生命拿来赊账,提前兑现到了二十岁,虽然不知道比例,但四舍五入就是一天当两天过,青春无限续杯。
我不用白条不借花呗,还是落入了提前消费的陷阱。莫名其妙地想起银翼杀手,“一半的长度,双倍的闪耀”。
为什么熬夜?因为半夜的时间是我悄悄咪咪从白天里偷来的,是我从庸常的生活手上硬生生抢过来的,它们都是我暗淡生命的辉煌延伸。
漫漫长夜时间永恒,早起之后屁事多多。我好喜欢熬夜,我把它当成生命的延展。
白天我太累太窝囊,时间也被研磨得太碎。而夜晚的时间终于变得纯粹,整块整块的。质地均匀,毫无杂质,一切琐碎的沉淀下来可以不讲效率、随心所欲地浪费。
十二点是熬过今夕与昨夜的分界线,而凌晨一点,仿佛是跨过了生活与生存的交界处。
写这段时,就是凌晨一点。
凌晨一点只有一个坏处,它太安静了,安静到能轻易挑起汹涌的思绪。我变成旷野上唯一的稻草人,而反复纠缠的鸟群忽而又至。
记忆比我家的狗还听话,只要做出扔的动作,它总能从以前捡点东西回来。
蜷缩在夜色里,就像躲进儿时的被窝。
那时窗外灯火影影绰绰,夜空是紫罗兰一样的沉沉靛蓝,东方红大桥上偶尔传来遥远的汽笛,铁牛广场上的灯光绵延,一直延伸到涪江的那一边。而涪江,它比时间流得更慢。我的小床安稳,日子粘稠又缓慢。
那时我不想实现什么价值,只是希望明天可以玩得更开心一点。小时候打街机,三国无双,黄忠很菜赵云很强,一把币几包辣条一瓶可乐,玩到暮色沉沉,玩到看见奶奶黄昏里拉长的影子。
到底是什么把我深深埋在忧郁里。
说起忧郁,初中晚自习,有个大叔在门口和我的班主任求了很久,想让孩子进我们班,他几乎抽掉整整一盒烟也点不燃夜晚,熄灭的烟头是掐灭的念头。他牵着的小孩在门口矗立,攥着摞厚厚的奖状,沉默得像一段长满青苔的枯木。
忘记哪个心理学家说过,同情的本质其实是这件事尚未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侥幸,我深以为然。还好那个小孩不是我。
后来某次考试,九门课,一共九百分的满分,年级第一考了808分,听见这个数字的瞬间,主观上世界停顿了半秒,像电影里那样,嗡的一声,大脑空白。
多少?
那是某个初夏的平常中午,隔壁床的人用讲乐子的平淡语气告诉我的。我上铺的哥们在洗鞋,水龙头哗哗响,床板一如既往地嘎吱嘎吱叫,有谁刚刚撕开了一袋辣条,满屋飘香。808这个分数似乎从来不存在,大家不以为意。
室友说,哎呀没事的,我们又不跟他比。
我很清楚,自己当然不可能争第一,这对我的排名造不成任何实质影响,他考多少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却仍然没来由地陷入剧烈的痛苦当中,头皮实实在在的发麻,就像脚下的地面突然塌陷,恐惧爬上心头。
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有些事居然真的不是我能改变的,哪怕献出我的一切都不够。
未来的剧本已悄然写好,在痛苦的思考中向我掀开一角作为预告,而在自己花大钱提前点映后,却看到了最烂的结局。
那时我重复最多的动作就是坐下。坐在学校的椅子上,开始一天的课程,下课就是做题,也很少动;周五放学,马上去坐到补习班的椅子上,开始不同的查漏补缺,学到十点,在回家的车上,我常常会睡着;周六,坐到家里房间的椅子,又是几个钟的作业和所谓自我提升时间,爸爸妈妈夸我懂事;至于周日,我就要回学校了。
阳光照不透窗口的树叶,所以屋里有点黑,让我想起那个不算太遥远的夜晚,那个抽烟的父亲,那个沉默的孩子,那样的无力感,一点一滴,实实在在地渗进我的骨髓。
我发觉我的老师兢兢业业,他们的责骂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我们好,我的父母管我也只是想我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我的生活已经比他们好千百倍。
他们谁都没有错,可是我也没有错,只是有人能考出808,而我永远考不出808。
这是根本上的无能为力,是不能消除的系统误差,是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
我的叛逆期骤然结束,太过于简单干脆了,就像关上了某个开关。与此相对的是,这件事在一瞬间就改变了我的性格,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黑色幽默,从此和我如影随形。
我变成一个喜欢在苦难面前嬉皮笑脸的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第一反应先是笑,因为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消解很多意义——很多事从根源上被解构以后,极端来说,无外乎管我什么事和管你什么事。
“黑色幽默是一种荒诞的,把痛苦与欢笑、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的喜剧。”
哈哈,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每个清醒的凌晨一点,我只是在害怕迎来又一个不可知的明天。
醒悟的时候才最困顿,意识到自己挣扎在最普通的无力感里,多少年穿林打叶,佯装着轰轰烈烈,一路上花开花落,又侥幸地起起跌跌。
我的文字似乎也快要从我笔下背井离乡。硬着头皮遣词拼凑,写出的都是好烂的比喻,词不达意的一口枯井。我挤出来的东西要么太寡淡要么太晦涩,段落与段落间气若游丝,一写东西顿感笔锋无力,我在期待什么呢?
我好羡慕王小波余光中海子,我喜欢他们的多感,个人意志可以在干净的文字里毫不费力地闪耀,所有意象就乖巧地蹲伏在他们膝下,事物间隐秘的联系晓若晨星,于是苍茫来事,信手吟游。
博尔赫斯说过,好的作品会唤起读者的感觉,不是描述在下雨的事实,而是被雨淋湿的感觉。王小波也说,要是一个作家沉迷于搜肠刮肚地找出各种形容词,他就完了。
我写东西的时候,要是准确抓住那样好的文字,哪怕只有一句,肯定会开心好几天。而且每每想到,多半还要窃喜着再拿出来咀嚼。
我的神来之笔,只是别人的史不绝书。
我的月亮,又是谁的床头灯。
我一直在和自己和解,不管再怎么失望,也要尝试接纳理想的落差。就像再怎么熬夜熬到凌晨一点,迟早也要沉沉睡去,不然是要猝死的。
对于不切实际的未来,我仍然擅自抱有不多不少的期许。就像我以前一直期望着能过上诗一样的生活,好消息是过上了,坏消息是后期杜甫。
在高考前,活在巨大的压力下,似乎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有限的,要是不豁出命去抢就拿不到。所以我以为,如果考不出808,自己的追求就不可能实现,我想要的都会被无一例外地摧毁掉。
我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海子,喜欢“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喜欢与我一拍即合的,繁杂又暴烈的情绪。那时我对他能写出“劈柴喂马周游世界”感到十万分的不可思议。直到今天,我才终于开始理解。
对完美的执念终将困我一生,但那又怎么样,我根本不需要去打败完美的人,对普通人而言,世界的资源是太过饱和的,任何一只狮子都不需要去抢机器人的大号电池。
生活不是要咬牙切齿地和谁去拼刺刀,也不是要去记恨谁。要实现自己的意志,不意味着要“反抗什么”,“拼命做什么”。很多时候这并不是好事,它会带来懒惰和优柔寡断。但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休克疗法。
呼吸式的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且把它当做最平常的事情,从追求完美,变成追求小小的欢喜和一星如豆的温暖。
这是某种意义上的悲剧,但不太明显。可以忽略不计。想起加缪说过,悲剧是人生的开胃酒。
所以,我还在装模作样地写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笼络起零零散散的词句,不是因为我想让自己的文字不朽,只是让它们充当我和世界之间的双面间谍。
所以,我还在想,也许是时候要振作精神,试着去打一次ACM了,哪怕打不好也无所谓,再也不会有人指着鼻子骂我。
把酒换新,把心换旧。背起行囊,打出名堂,我也要收拾旧山河,圆起青春的谎话。
此时窗外风雨大作,重庆到十一月终于开始有一点冷,睡觉要盖厚被子了。
已经写到了两点,居然还没写完,那标题就取凌晨一点遗事吧。
文学性的残片还在纠缠我,没救了,意识流好像写过头了,这个话题改天再写,明天还有课,我要先睡个觉。
平静似水的夜里,我心底的一部分正在死去,和刚刚过去的凌晨一点一样,悄悄地永远消失不见,只留下些一时半会捉摸不透的感觉,像流水或轻烟,海波或浅雪,晨雾里开遍鲜花的原野。
青年的一切腐烂都是为了抽芽,早该见怪不怪。就由他去风雨飘摇吧。
总会有那么一天,只为了热腾腾的早餐就热切地期盼日出,我站在金色的天空下,美好如期而至。
已经到了钟表划定的时刻
该换乘到黎明的车厢了
带不走往昔的你
归处只有浪漫的土地
月亮的踪迹就在彼端
缥缈的心
就把它交给凌晨一点的星空吧
或凌晨两点
来者不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