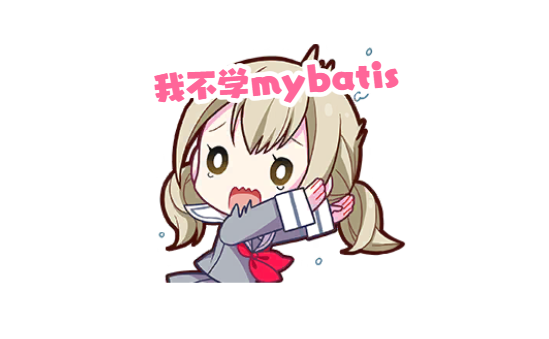写在二十岁
日子稠密,把我的身体当做容器,
裹起一层一碰就响的铁皮,
它埋伏着五十年后致命的暗伤。
待价而沽的,是沉默的人,萧条的人,
是二十岁的人
我还以为在每个人的二十岁,变得光芒万丈是顺理成章的事呢。
面对着席卷而来的命运,我照样只会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寻求逃避。如果可以,我还是很情愿大哭大闹的。根本不会有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也不会有任何机械降神的反转桥段,被寄予厚望的一切戏剧性都不存在。
偷一句村上春树的话,我一点也没做好二十岁的准备,挺纳闷的,就像是谁从背后把它推给了我一样。
现在这个满二十岁的人,是谁都行,可是,可是,怎么会是我。
小时候,幼儿园老师问我,你觉得什么样才算是长大了呢?
多简单,十八岁就是长大了。
两个老师看着我笑了起来,那个笑太清晰,我今天都忘不掉——过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好像在说:这个笑就是标准答案啊。
我慌了,改口说,那就是二十岁。
他们还在笑,不置可否。
别笑了!你们倒是告诉我啊!我真二十岁了,怎么还没长大。
计划要坐大巴去木格措,所以我偷偷摸摸地提前吃掉了自己的生日蛋糕。我的蛋糕上只插着两根蜡烛。
小时候,有一次我爸过生日,我攒了好久的钱,给他买了个大蛋糕。该插蜡烛了,他只插了四根。我说真没意思,我专门拿了很多蜡烛呀。
我爸说,就插四根,四根意思意思就够了。
我说,大人都是这样的啊?多少岁就应该插多少蜡烛,这样才能好好记录自己是怎么长大的。
他没理我,只是点燃蜡烛,准备直接吹灭,我抢着说,这时候应该许个愿呀。
我爸终于噗嗤一声笑出来,看看我妈,又看看我,顺从地眯上眼开始许愿。沉默片刻,神色意外的肃穆,然后猛地吹出一大口气,火苗噗的一声消失。
“你到底许了什么愿望啊?”
“说出来就不灵了。”
看着面前的蛋糕,不得不承认,我也已经变成了不喜欢过生日的大人。
我害怕看着整整二十根蜡烛在面前摇曳,它们明晃晃地提醒我:你现在二十岁,要承担责任,不许逃避。
原来在二十岁时,“长大”已经结束了。一尊雕塑,在铸成的那一刻就已经停止创作,剩下的岁月只是漫长的磨蚀。
现在的生日不再是“长大”的里程碑,是催人“成长”的倒计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青葱无恙,尽数典当。难释怀的事,早早扯断了我与往昔之间那根细细的风筝线。
坐在长途大巴上写这些时,又看见窗外有个磕长头的人。和我以前看见过的一模一样,衣服很脏很烂,胡子和头发一起飘飞。一步一磕,晃悠悠,背上巨大的转经筒一直替他沉默地祝祷。嘴里无声的吟哦,随风直上高原的悠远天空。
他的愿望好纯粹,干净得像是远处高山上,亘古不化的雪。他就在车窗外一闪而过,融化在山野间迷蒙的雾里。
我突然想到,那时之前吃蛋糕时该许个愿。
穿过雾气,康定汽车站旁边的青年旅舍里,一间小房里奇迹般挤下了六个大学生。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谈天说地,慢慢熟络了起来。聊最俗气的人生和理想,谈川西,讲喜欢的女孩子,从摇滚聊到罗马法去。
最后我说,我一直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去川西。只玩三天,甚至谈不上浮光掠影。没做攻略前,我根本不知道木雅圣地是什么地方,也没听过折多山或木格措。
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点:给人以离家很远的疏离感,和浪漫无关,和救赎更不接壤。
大概在心底里,我其实只是想去很远的地方。暂时摆脱我小小的、固定的生命轨迹——街口来往的车,石灰石斑斓的地板,教室的嘈杂声音。
我不希望描绘到最后时,才发现我的生命里原来只剩下一个社区、一个房屋、一个卧室,甚至只是一张床。
我问,你们为什么来川西?
不许说青春啊理想啊之类的废话。
大家一时失语,支支吾吾,语焉不详。
我把磕长头的人描述给他们,说,我补许一个生日愿望吧。我希望自己能永远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木格措,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二十岁,我应该开始为自己活着,而活着的花应该有一万种开法。
我上铺的哥们嬉皮笑脸地锐评说,我好像对生命的大走向无所吊谓,却对细枝末节斤斤计较。
我说也挺好,我们各自还有一生的奇迹。
这句是偷的后海大鲨鱼的歌词,但是他们没听过,惊呼我这句话帅闷了啊啊啊!
深深地吹一口气,吹熄生日蛋糕上的两根蜡烛,我爸怎么吹的,我就怎么吹的。
二十年的岁月,二十年的时光,二十年的细碎悲喜,原来只是那样轻的呜咽。
这种时候,似乎该写点什么、说点什么。
可是我欲言又止,怕自相矛盾。
真奇怪啊,命运,它居然是自顾自的摆拍。
我一瞬间知道了我爸那年的生日愿望,答案简直已经写在谜面上——一定是祈愿着我的未来。毕竟我是父母这对中年夫妻周身上下唯一相同的顽疾。
可二十岁以前,我根本不会想到这里去。它们对那时的我超纲,不回答也不扣分,毕竟夏虫不可语冰。
但是我不是虫,我能活到冬天的。
写这段的时候,青旅里的人还在睡觉,我要赶最早的一班大巴去成都的音乐节。
康定的清晨真的很冷,折多河奔腾翻涌,整座城半睡半醒,沉默地吞吐雾气。四下连绵的群山若隐若现,天空淡得像褪了色,川西仍然是我悬而未决的谜。
走在路上,我感觉自己正变成一个将错就错的通假字,等待着被谁好好地解释,又被谁完整地接受。
谁有想起我,谁有讲起我,谁有唱起我。
谁有忘记我,谁有妄议我,谁有藏起我。
偷一句余秀华的诗,反正是绚烂,反正是到来,反正是背负着慢慢凋残的孤独,耀眼的孤独,义无反顾的孤独。
在成人之前,多想先成为自己。
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