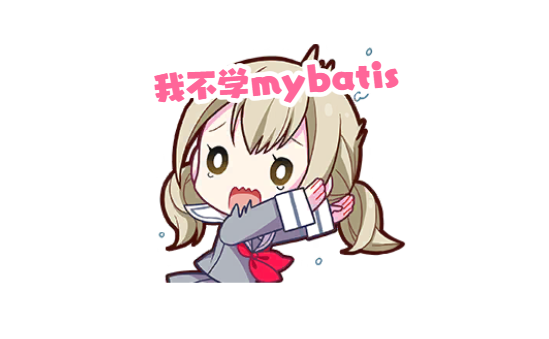夜食小记
选修课下课,排队等校车的人密密匝匝,多得能把我淹死。反正就在校门口,不如去天生丽街的夜市逛逛。
说实话,我对逛夜市没什么特别兴趣,因为全国各地的夜市好像都长一个样:人挤人,各式灯带流光溢彩,苏联解体音质的喇叭响个不停,眼前是油腻腻的袋子和模糊的面容。
明明已经知道里面都是什么:狼牙土豆、凉皮凉面、臭豆腐、羊肉串、烤面筋,再来点网红标签,还能有什么意思?
但是很奇怪,一到这种地方我总是走不动路,不吃点东西宛若受了刑。
谁有本事拒绝眼皮底下的浓油赤酱?脆生生的烈火烹油是我们天生的软肋。太质朴太简单——只要猛火弄熟,皮鞋都好吃啊。
世上早有姜、葱、蒜、盐、酱油、酒、醋、豆瓣酱、辣椒、花椒等等等等为食材点石成金的法宝,但到最后,所有调味料和食材都无法取代的,还是在人声鼎沸里花了时间,好好做出来的,最俗气的烟火气。
我扯着嗓子要了一份火爆大鱿鱼,多加辣。老板嚷嚷着说前面可排了不少人别急着点啊,我说不急,我先自己乱逛一会。
走在夜色里,看着小摊的灯,眼前影影绰绰,我以为很多事早就该忘了,可回忆的雾气分明来自多年之前。
小时候一家人自驾去北海,开车开到很晚,天彻底暗下来,我们在某个贵州和广西的边界城市歇脚。
那座小城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有好多好多停摆的厂房,不少建筑横七竖八地排开,黑漆漆的,像是某种巨兽的躯体。
我饿肚子了,早在高速上就嚷嚷着要找东西吃。在路边找到了几家大排档,很特别,它们开在一些很大的工棚里,像是某个厂没搬完剩下的。铁锈的味道隐约传入鼻腔,天花板高得离谱,只架着几口孤零零的灶台,看上去空空荡荡,显得不太协调。
座位倒是不少,一次性桌布上是黑乎乎油腻腻的塑封菜单。其实这种地方,菜单根本没什么用,都是说什么炒什么。我要了一份炒河粉。老板应了一声就回灶台埋头开炒,信手抓料,火舌呼呼地撩出来。
炒河粉上桌,牛肉肥厚,蒜苗油润,河粉透亮,咸鲜带甜,又脆又韧。夹一筷子一口下去,牙齿像陷进去似的,有嚼劲又滑润,特别是蒜苗嚼到唧唧吱吱响,越吃越想吃。
环顾四周,上座率挺高。没上菜前,吹牛的醉酒男人,缩在墙根下偷偷抽烟的高中生,月光沉默地在他们身边投下阴影。不再冒烟的工厂墙壁上画满涂鸦,让人想起百年孤独里那个最后老得动不了,只能被小朋友当玩具的乌尔苏拉。
我就着饮料吃下最后一口。从此再也没吃过这么香的炒河粉,这东西不讲配方,讲个劲头。
后来在上海,晚上在南京路游荡觅食,误打误撞拐进一个小巷子,意外发现了家馄饨店。
听说以前的老上海,晚上馄饨挑子过,楼上放个篮子,篮里放钱,馄饨挑子就将一碗馄饨放进篮里,提上去当宵夜,吃个肚饱暖,睡觉,多好。
要一碗小馄饨,老板就打开木头锅盖,从热气喧腾的锅里盛一碗出来,好像加了酱油、紫菜、虾米和麻油。
这家的小馄饨和四川这边的不一样,它的讲究只在汤与皮,馅不过小小一抹肉。只要汤鲜,皮滑就行。馄饨像金鱼似的飘荡,软若无物,滑溜带烫,不用勺子舀来吃,吸一口就全下去了。其实也就借个味过个口瘾而已。
喝完一碗小馄饨,在店里懒洋洋地歇着,店里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人,点好单,沉默着坐下,吸溜吸溜喝完馄饨又沉默着离去。
有个阿婆像是熟客,用上海话讲了不少,我只听懂一句“吃个汤头葱花香”,一直记到今天,因为她好像踩中了诗的韵脚。
馄饨店灯光昏黄,装修用了许多木结构,似旧非旧的感觉让人着迷。它笼络了多少寂寥的胃啊。
以前和爸妈晚上出门逛街,那会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正在闹矛盾,遇到门口有个小哥在摆摊卖凉虾。
天气闷热难耐,正好点了碗凉虾,加西米露和小汤圆,多放红糖和醪糟。
第一口先小心翼翼吸一口,别让水冒出来了,也把干得发响的嘴润一润。
这样第二口就好端着碗,猛地来一口大的。甜而又冰,满嘴冰凉,又有醪糟那股酒味,杀舌头,不觉就嘴发丝丝声,太阳穴都冰得发痛,这才叫做真痛快。
这时候已经解过了瘾,再喝太快会败胃口,所以要徐徐喝第三口第四口,咕咚咚下肚,凉虾滑溜溜,满嘴甜得透透的。矛盾还在吗?好像已经不重要了。
第二天再去喝凉虾,没有找到他。后来他再也没有来过。
爸妈调侃说,这小伙子,一点定力都没有,应该是生意不好就不来这里了,真的是。
没来由地想起这些事,也没来由地想起了很多人,想起我与他们偶然的交错。
广西边界小城的青年,生活的风沙把你们吹到了哪?
吹牛的大叔,你的酒又醒了多少?
上海的阿婆,还常去那家馄饨店吗?
卖凉虾的小哥,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这些答案我都无从知晓了。就像是上一秒才凭空闯入千千万万原本无关的命运,下一秒就已经匆匆掠过。可以唯心地说,我们唯一的联系就是我断断续续的记忆。
这些记忆显然也是不可靠的。凭我的记性,或许我根本没有去过那些工厂里的大排档,这只是我的一场梦;又或者是我记错了在电视里看过的片段,把它当成了我的经历。
更要命的是,现在只有我会记得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所以我也无从证实它们是否真实存在,这成了我生命里的一桩桩悬案。
然而,我还是愿意相信我的记忆。在我再一次忘记它们之前,这都会是一种微妙的心照不宣。
我的记忆维持着一段过往存在的可能性。也许就在某一个不起眼的瞬间,那些似是而非的往事在消逝和存续的十字路口上停滞不前,而我正挠着脑袋苦苦回忆:哎那天我干什么了来着?
这种感觉让人着迷。
是时候回去拿我的火爆大鱿鱼了。
想了这么久,为什么火爆大鱿鱼还没叫到我?去问老板。
原来她把我忘了。